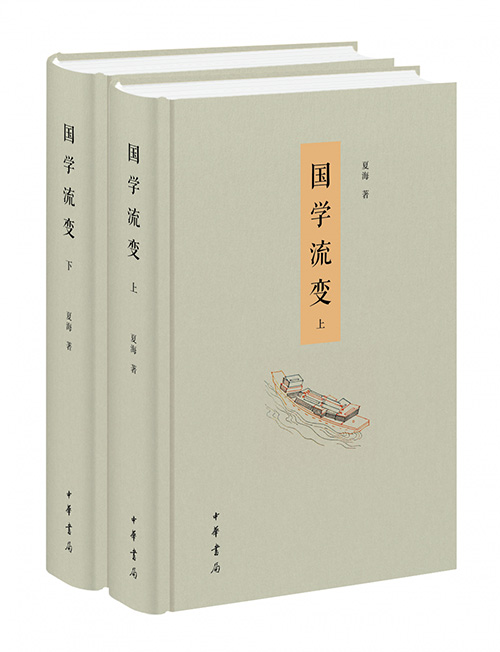
作者:夏海
出版社:中华书局
出版时间:2024年6月
开本:特32开
装帧:精装
字数:800千
推荐语
一部简明且系统的中国思想史。
探寻国学流变,让灵魂得到净化,思想得到升华,人格得到镕铸。
作者简介
夏海,浙江安吉人,法学博士。1978年入中山大学哲学系学习,1982年分配到中央国家机关工作,1999年考入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攻读博士学位。长期从事国学和传统文化的研究工作,出版多部著作,主要有《论语与人生》《品读国学经典》《老子与哲学》《国学要义》《孟子与政治》《国学溯源》《韩非与法治》等。
编辑推荐
1.对中国思想发展脉络进行了系统梳理,分为先秦诸子、汉朝经学、魏晋玄学、隋唐佛学、宋朝理学、明朝心学、清朝朴学七大板块。
2.每个版块均以历史背景+社会思潮+代表人物的形式呈现,体例新颖且完整有序。
3.阅读方式灵活多样,可以按板块的先后顺序依次阅读;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要,或集中阅读历史背景,或集中阅读社会思潮,或挑选代表人物阅读。
4.文字简洁晓畅,史论结合,集学术性、普及性、思想性于一体。
内容简介
《国学流变》实为中国思想小史,它以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思潮演变为线索,围绕人性论、天人关系以及人与社会关系,探寻传统社会学术思想的发展变化轨迹和规律。
书中“绪言”概述思想史研究的对象、内容和方法。全书主体共分七章,即先秦诸子、汉朝经学、魏晋玄学、隋唐佛学、宋朝理学、明朝心学、清朝朴学。“余论”部分简述明末尤其是1840年以来,西学东渐对于传统社会学术思想的影响和变化,以及人们对于中学与西学及其相互关系的复杂看法。
主体中的每一章均由三个板块组成,即时代背景、社会思潮和学术思想代表人物。时代背景力图囊括影响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各种事件,社会思潮努力描述当时社会的所言所行、所思所想,代表人物则包括思想家的生平事迹及其思想范畴和学术观点。
阅读国学流变,我们可以系统了解中国传统社会的学术思想脉络,体会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,进而让灵魂得到净化,思想得到升华,人格得到镕铸!
自序
《国学流变》实为一部中国学术思想简史。研究著述过程辛苦,收获却是硕果累累。最大的收获就是充分领略了中华文明的无限风光,深切感悟了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。
按照黄帝纪年,中华文明已有五千年历史,人们比较熟悉的上古文明有黄帝、炎帝、唐尧、虞舜和夏、商、周三代。即使有文字根据的上古文明,也可追溯到商朝的甲骨文,约为三千五百年历史,商朝已确立比较完整的中国文字书写系统。上古文明的完成则在周朝,其建立的礼乐文化和血缘宗法制度,积淀为传统社会和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。面对如此悠久绵长、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,作为炎黄子孙,我们骄傲而自豪。
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历史的文明,汉字功不可没。文明的主要载体和标志是文字,中华民族把文字诞生看成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件。黄帝史官“苍颉作书,而天雨粟,鬼夜哭”(《淮南子·本经训》),犹如天降粮食大雨,百鬼夜里哭泣。汉字是世界上持续使用时间最长的文字,也是上古时期各大文字体系中唯一传承者。汉字是象形文字,经历了从表形到表意再到形声的造字过程。仓颉“见鸟兽蹄迒之迹,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,初造书契”;“仓颉之初作书,盖依类象形,故谓之文。其后形声相益,即谓之字。文者,物象之本;字者,言孳乳而浸多也”(《说文解字叙》)。当然,汉字不是个人的创造,而是中华民族集体的智慧。在汉字的发展过程中,甲骨文具有里程碑意义。甲骨文是商朝后期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,现已发现约15万片甲骨和4500多个单字,其中能够识别的为1500个单字。甲骨文初步建构了“象形、会意、形声、指事、转注、假借”的造字方法,展现出汉字独特的魅力。秦始皇“书同文”政策具有关键作用,不仅统一了文字,巩固了政治统一,而且为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夯实了根基。汉字最大的特点是结构稳定,深具时间和空间巨大的穿透力和凝聚性。在时间上,汉字古今一贯,能够顺畅地串联起中国悠久的历史;在空间上,汉字四海一贯,能够顺畅流泻于九州大地,沟通不同的方言,更能沟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。我们应当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汉字。
文明的核心是学术思想。任何文明的发展都是学术思想的创新和进步,而学术思想的停滞,必然导致文明的衰落,乃至湮灭于历史的长河之中。先秦时期,中华文明的天空群星璀璨,诸子百家争鸣,建构了博大精深的学术思想体系。他们是儒家、道家、阴阳家、法家、名家、墨家、纵横家、杂家、农家(《汉书·艺文志》),与世界上其他文明的先哲们一起造就了“轴心时代”,发生了“终极关怀的觉醒”([德]卡尔·雅斯贝斯著,魏楚雄、俞新天译:《历史的起源与目标》,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,第8页)。由于诸子百家的学术思想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,能够在历史长河中吸收消化融合外来文明和异族文化,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提供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。中华文明吸收消化了佛教文明。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,于西汉末年传入中国,“汉哀帝元寿元年,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《浮屠经》曰复立者其人也”(《三国志·魏书·乌丸鲜卑东夷传》裴松之注引鱼豢《魏略·西戎传》),逐步融入中国文化,最后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至于异族文化,中国历史上有过多次少数民族入主中原,他们不仅没有消解中国文化,反而被中国文化所融合,进而为中华文明贡献了养分,补充了新鲜血液,使得中华文明更显旺盛蓬勃的生命力。开放包容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原生密码,只有开放包容,中华文明才能在历史长河中不择细流,奔涌向前。
“汤之《盘铭》曰:苟日新,日日新,又日新”(《礼记·大学》),创新发展促进和保障了中华文明源远流长。中华文明自诞生之日起,从来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,而是适应时代需要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,学术思想不断推陈出新,引领中华民族前行。先秦诸子百家之后,先是发展出汉朝经学。汉武帝在秦朝统一政治的基础上,统一了思想文化,“孝武初立,卓然罢黜百家,表章六经”(《汉书·武帝纪赞》)。汉朝经学是先秦儒学的第一次更新,重视注释经典的名物。次是发展出魏晋玄学。魏晋南北朝的名士们不愿受到名教束缚,而要崇尚老子、庄子,清淡玄理,不务实事,追求个性和自由,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(嵇康《释私论》)。再是发展出隋唐佛学。佛教自西汉传入五百年后,经过格义会通,终于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,形成了中国的禅宗,“但持《金刚经》一卷,即得见性,直了成佛”(《坛经》)。继之发展出宋朝理学。宋朝理学家以儒学为基础,汲纳佛、道精义,主张性即理,贯通哲学、历史、伦理、教育诸学科,建构了庞大精微的程朱理学体系。宋朝理学是先秦儒学的第二次更新,注重阐述经典的义理。随后发展出明朝心学。心学属于理学的范畴,阳明心学与程朱理学的差异在于心、性谁为形上本体的不同观念。传统社会末期,则是发展出清朝朴学,致力复归于汉学注释经典的传统。创新发展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原生动力,只有创新发展,中华文明才能在世界格局中占据主动,赢得未来。
现在,中华文明又一次站在了创新发展的历史关口。自1605年利玛窦编辑出版《乾坤体义》算起,西学传入中国已有四百多年历史;自1840年中国迈入近代化算起,西学传入中国已近二百年历史。西学东渐,西方文明的输入,使得中华文明面临严峻挑战和难得机遇。中华文明曾经从容应对了佛教文明的挑战,必将坚韧不拔地应对西方文明的挑战。只要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地位不动摇,坚持学习吸收消化融合西方文明不停步,开放包容、创新发展,中华文明就一定能够走向世界,再创辉煌。
是为序。
夏海谨记于癸卯年夏月
精彩选读
王阳明的致良知和知行合一
一、致良知
致良知是王阳明平定宁王之乱后全部思想的结晶。他50岁时,居江西,“是年先生始揭致良知之教”;“自经宸濠、忠泰之变,益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难,出生死,所谓考三王,建天地,质鬼神,俟后圣,无弗同者”(《年谱》)。致良知思想的产生,则与朱熹的格物致知之学有关。朱熹认为,修身养性先要向外格事事物物,进而“即物穷理”。王阳明龙场悟道后,认为良知自我完具,不假外求,只须内求,“先儒解格物为格天下之物,天下之物如何格得?且谓一草一木亦皆有理,今如何去格?纵格得草木来,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?”(《传习录下》)
儒家的理想人格是圣人和君子,格物致知的目的也是成人成圣。儒家认为人人可以成圣,孟子说“人皆可以为尧舜”;“尧舜之道,孝弟而已矣。子服尧之服,诵尧之言,行尧之行,是尧而已矣”(《孟子·告子下》)。荀子也说“涂之人可以为禹”;“凡禹之所以为禹者,以其为仁义法正也。然则仁义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,然而涂之人也,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,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,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”(《荀子·性恶》)。对于如何成人成圣,孟子与荀子却发生了分歧,孟子是思以成圣,“心之官则思。思则得之,不思则不得也。此天之所与我者,先立乎其大者,则其小者弗能夺也”(《孟子·告子上》)。其方法为存心养性,“存其心,养其性,所以事天也”(《孟子·尽心上》)。荀子是学以成圣,“吾尝终日而思矣,不如须臾之所学也;吾尝跂而望矣,不如登高之博见也”(《荀子·劝学》)。其方法为化性起伪,“凡性者,天之就也,不可学,不可事;礼义者,圣人之所生也,人之所学而能,所事而成者也。不可学、不可事而在人者,谓之性;可学而能、可事而成之在人者,谓之伪,是性伪之分也”(《荀子·性恶》)。思以成圣认为道德的根源不能从外部去寻找,必须从生命内部探求,因而思是确立道德生命的根本途径;学以成圣则认为道德生命必须借助外部力量才能确立,因而学是确立道德生命的主要途径。王阳明承继了思以成圣的路径,从思以成圣的角度解读格物致知,得出了致良知的结论,建立起心学的修身论,“近来信得致良知三字,真圣门正法眼藏。往年尚疑未尽,今自多事以来,只此良知无不具足。譬之操舟得舵,平澜浅濑,无不如意,虽遇颠风逆浪,舵柄在手,可免没溺之患矣”(《年谱》)。
王阳明从小就立志做圣人。在王阳明看来,圣人犹如人是完人,金是足赤,“圣人之所以为圣,只是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。犹精金之所以为精,但以其成色足而无铜铅之杂也。人到纯乎天理方是圣,金到足色方是精”。圣人虽有分量不同,却无成色不同,“然圣人之才力,亦有大小不同,犹金之分两有轻重”;“分两虽不同,而足色则同,皆可谓之精金”。所以人人都可以学做圣人,都可以成为圣人,“以夷、尹而厕之尧、孔之间,其纯乎天理同也”;“故虽凡人而肯为学,使此心纯乎天理,则亦可为圣人。犹一两之金比之万镒,分两虽悬绝,而其到足色处可以无愧,故曰‘人皆可以为尧、舜’者以此”(《传习录上》)。王阳明以镜子为喻,说明圣人与常人的差别在于有无尘埃,圣人之镜无尘埃,常人之镜有尘埃,“圣人之心如明镜,纤翳自无所容,自不消磨刮。若常人之心,如斑垢驳蚀之镜,须痛刮磨一番,尽去驳蚀,然后纤尘即见,才拂便去,亦不消费力。到此已是识得仁体矣。若驳蚀未去,其间固自有一点明处,尘埃之落,固亦见得,才拂便去。至于堆积于驳蚀之上,终弗之能见也”。王阳明指出,学做圣人,就是要拂去尘埃,廓清心体,“学者欲为圣人,必须廓清心体,使纤翳不留,真性始见,方有操持涵养之地”(《年谱》)。而廓清心体的方法不是静坐思虑,而是致良知,清除私念和私欲,“俟其心意稍定,只悬空静守,如槁木死灰,亦无用。须教他省察克治”;“如去盗贼,须有个扫除廓清之意。无事时,将好色、好货、好名等私欲逐一追究搜寻出来,定要拔去病根,永不复起,方始为快。常如猫之捕鼠,一眼看着,一耳听着,才有一念萌动,即与克去,斩钉截铁,不可姑容,与他方便。不可窝藏,不可放他出路,方是真实用功,方能扫除廓清。到得无私可克,自有端拱时在”(《传习录上》)。
致良知思想是孟子良知与《大学》致知的结合。孟子以良知论证人性善,“人之所不学而能者,其良能也;所不虑而知,其良知也。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,及其长也,无不知敬其兄也。亲亲,仁也;敬长,义也;无他,达之天下也”(《孟子·尽心上》)。《大学》强调致知是修身的重要环节,“欲修其身者,先正其心;欲正其心者,先诚其意;欲诚其意者,先致其知;致知在格物”。在良知方面,王阳明沿袭了孟子的良知概念中的孝道和性善内容,“心自然会知,见父自然知孝,见兄自然知弟,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”(《传习录上》)。同时,发展完善了良知概念,认为良知不仅是孝道和性善,而且是绝对本体,等同于易,是一个统贯天人、包罗物我的最高范畴,“良知即是易,其为道也屡迁,变动不居,周流六虚,上下无常,刚柔相易,不可为典要,惟变所适。此知如何捉摸得?见得透时,便是圣人”(《传习录下》)。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,“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,只是一个真诚恻怛,便是他本体”(《传习录中》)。良知还连通着天命之性与万物一体之仁,“是其一体之仁也,虽小人之心,亦必有之。是乃根于天命之性,而自然灵昭不昧者也,是故谓之明德”;“故夫为大人之学者,亦惟去其私欲之蔽,以自明其明德,复其天地万物一体之本然而已耳”(《大学问》)。在致知方面,王阳明主要继承了《大学》的致知概念,认为致知是彰显良知本体,“然在常人,不能无私意障碍,所以须用致知格物之功,胜私复理。即心之良知更无障碍,得以充塞流行,便是致其知。知致则意诚”(《传习录上》)。致知是去除气禀物欲对良知的遮蔽,“人心是天渊。心之本体无所不该,原是一个天,只为私欲障碍,则天之本体失了。心之理无穷尽,原是一个渊,只为私欲窒塞,则渊之本体失了”(《传习录下》)。致知是推致良知于事事物物,致良知是格物,格物是正念头,“致知云者,非若后儒所谓充广其知识之谓也,致吾心之良知焉耳”;“今于良知所知之善恶者,无不诚好而诚恶之,则不自欺其良知而意可诚也已。然欲致其良知,亦岂影响恍惚而悬空无实之谓乎?是必实有其事矣。故致知必在于格物”(《大学问》)。
致良知的关键是诚意。朱熹区别心与理,所以要求先格事物之理,然后获得普遍之天理,“所谓致知在格物者,言欲致吾之知,在即物而穷其理也”(《大学章句·补格物传》)。在事物之理升华为普遍天理的过程中,朱熹强调敬的作用,“人能存得敬,则吾心湛然,天理粲然,无一分着力处,亦无一分不着力处”(《朱子语类》卷一二)。王阳明不同意朱熹割裂心与理、物理与天理的联系,认为诚意能使心与理、物理与天理合一,而朱熹的《大学》新本是“先去穷格事物之理,即茫茫荡荡都无着落处,须用添个‘敬’字方才牵扯得向身心上来,然终是没根源。若须用添个敬字,缘何孔门倒将一个最紧要的字落了,直待千余年后要人来补出?正谓以诚意为主,即不须添敬字。所以提出个‘诚意’来说,正是学问的大头脑处”。王阳明以孝心与行孝的关系进一步说明诚意的重要性,凸显了主体选择道德行为的主动性和自觉性,“此心若无人欲,纯是天理,是个诚于孝亲的心,冬时自然思量父母的寒,便自要去求个温的道理;夏时自然思量父母的热,便自要去求个凊的道理。这都是那诚孝的心发出来的条件。却是须有这诚孝的心,然后有这条件发出来”。王阳明所谓的诚意,就是要避免功利之心,纯乎天理之心,“所以谓之圣,只论精一,不论多寡。只要此心纯乎天理处同,便同谓之圣。若是力量气魄,如何尽同得?后儒只在分两上较量,所以流入功利。若除去了比较分两的心,各人尽着自己力量精神,只在此心纯天理上用功,即人人自有,个个圆成。便能大以成大,小以成小,不假外慕,无不具足。此便是实实落落明善诚身的事”(《传习录上》)。
致良知的前提是良知。没有良知,致良知无从谈起,也失去了目标。孟子是良知概念的创立者,他以孩童自然而然爱父母、敬兄长为例论证良知的实存性。王阳明是良知的拥趸,认为良知是先天内在于人的道德之心,“此便是良知,不假外求。若良知之发,更无私意障碍,即所谓‘充其恻隐之心,而仁不可胜用矣’”(《传习录上》)。在《孟子》一书中,良知概念只出现过一次,并没有展开和论证,而王阳明则充分论证和发挥良知思想。王阳明认为,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,昭明灵觉是指良知与心、性、灵合而为一,“惟乾问:‘知如何是心之本体?’先生曰:‘知是理之灵处。就其主宰处说,便谓之心;就其禀赋处说,便谓之性;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,无不知敬其兄,只是这个灵能不为私欲遮隔。充拓得尽,便完完是他本体,便与天地合德。’”(《传习录上》)王阳明的良知与心同一,也具有本体和形上意义,即良知是天地的本原,没有良知,就没有天地。“良知是造化的精灵。这些精灵,生天生地,成鬼成帝,皆从此出,真是与物无对。人若复得他完完全全,无少亏欠,自不觉手舞足蹈,不知天地间更有何乐可代。”(《传习录下》)王阳明在与弟子讨论中指出:“良知本体原来无有,本体只是太虚。太虚之中,日月星辰,风雨露雷,阴霾饐气,何物不有?而又何一物得为太虚之障?人心本体亦复如是。太虚无形,一过而化,亦何费纤毫气力?德洪功夫须要如此,便是合得本体功夫。”(《年谱》)
更重要的是,王阳明把良知理解为是非之心,认为是非之心任何人都是具备的,古往今来都是相通的,“是非之心,不虑而知,不学而能,所谓良知也。良知之在人心,无间于圣愚,天下古今之所同也”(《传习录中》)。甚至认为良知的根本就是有是非之心,而是非之心就是要好善恶恶。好善恶恶是知善知恶进而为善去恶的基础,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活动方式,“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,是非只是个好恶。只好恶就尽了是非,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”(《传习录下》)。王阳明指出,好善恶恶和是非之心,必须要有诚意,“为学功夫有浅深,初时若不着实用意去好善恶恶,如何能为善去恶?这着实用意便是诚意”(《传习录上》)。凡是能够诚意地好善恶恶,便达到了圣人境界,“人但得好善如好好色,恶恶如恶恶臭,便是圣人”(《传习录下》)。黄宗羲解读是非之心,“所谓知善知恶者,非意动于善恶从而分别之为知,知亦只是诚意中之好恶,好必于善,恶必于恶,孰是孰非而不容已者,虚灵不昧之性体也”(《明儒学案·姚江学案》)。有了是非之心,就有了修身尺度和人生指南,“尔那一点良知,是尔自家底准则。尔意念着处,他是便知是,非便知非,更瞒他一些不得”;“良知原是完完全全,是的还他是,非的还他非,是非只依着他,更无有不是处。这良知还是你的明师”(《传习录下》)。有了是非之心,就有行为规范和价值准则,“夫学贵得之心。求之于心而非也,虽其言之出于孔子,不敢以为是也,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?求之于心而是也,虽其言之出于庸常,不敢以为非也,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?”(《传习录中》)在良知和是非面前,即使孔子也要尊崇。王阳明的心学敢于否定权威,确实具有张扬个性和解放思想的意蕴。
致良知的目的是内圣外王。如果说良知是先天的道德价值理念,那么,致良知就是修身理念与行为、过程与结果的集合,以达到内圣外王的目的。在内圣方面,王阳明认为,致良知要格物,而格物不是为了即物穷理,而是为了正其本心,“格者,正也,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。正其不正者,去恶之谓也。归于正者,为善之谓也,夫是之谓格”(《大学问》)。由于人之本心是正的,只有意念起时才会有善恶之分,所以正心的实质不是端正本心,而是端正意念,“盖心之本体本无不正,自其意念发动而后有不正。故欲正其心者,必就其意念之所发而正之”(《大学问》)。端正意念,就是要恢复心之本体,“如今念念致良知,将此障碍窒塞一齐去尽,则本体已复,便是天渊了”(《传习录下》)。在外王方面,王阳明认为,致良知是要治平天下,“心者身之主也,而心之虚灵明觉,即所谓本然之良知也。其虚灵明觉之良知,应感而动者谓之意,有知而后有意,无知则无意矣。知非意之体乎?意之所用,必有其物,物即事也。如意用于事亲,即事亲为一物;意用于治民,即治民为一物;意用于读书,即读书为一物;意用于听讼,即听讼为一物:凡意之所用,无有无物者,有是意即有是物,无是意即无是物矣”(《答顾东桥书》)。在内外结合方面,王阳明认为,致良知统摄了儒家修身的全部内容,不仅统摄了内圣,而且统摄了外王,使内圣与外王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,“此正详言明德、亲民、止至善之功也。盖身、心、意、知、物者,是其工夫所用之条理,虽亦各有其所,而其实只是一物。格、致、诚、正、修者,是其条理所用之工夫,虽亦皆有其名,而其实只是一事”(《大学问》)。
二、知行合一
知行合一是王阳明心学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如果说致良知是王阳明晚年思想的成熟用语,更能洞见心学本体之全体大用,那么,知行合一就是贯穿王阳明一生的生命行动准则,是自龙场创立心学体系之初,使其理论至臻圆融而一以贯之的不二法门。知行合一与致良知的表达方式不同,而本质上却可互相诠释,“吾良知二字,自龙场已后,便已不出此意。只是点此二字不出。于学者言,费却多少辞说。今幸见出此意。一语之下,洞见全体,直是痛快,不觉手舞足蹈。学者闻之,亦省却多少寻讨工夫。学问头脑,至此已是说得十分下落”(《刻文录叙说》)。龙场悟道后,王阳明前往贵阳文明书院讲学,“自龙场延公于文明书院,以教诸士。当是时,不惟贵阳诸士得闻所未闻,而文襄公之学亦由此深造远诣,至今贵阳称善教者必曰文襄。则阳明公切磨之功,固不可诬”(《(嘉靖)贵州通志》卷一一)。钱德洪认为,先生“居贵阳时,首与学者为‘知行合一’之说”(《刻文录叙说》)。知行合一是王阳明创立心学的标志,也是王阳明心学体系的基础。王阳明中年之后很少提及知行合一,原因在于知行合一已经融入致良知这一更为简洁凝练的命题。良知是知,致良知是行,致良知就是知行合一,诚如明儒刘宗周所言:“良知为知,见知不囿于闻见;致良知为行,见行不滞于方隅。即知即行,即心即物,即动即静,即体即用,即工夫即本体,即下即上,无之不一。”(《明儒学案·师说》)
知与行既是认识论,更是实践论,在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。最早的认识是《尚书》提出的“知易行难”。北宋程颐认为知难行亦难,“故人力行,先须要知,非特行难,知亦难也。《书》曰:‘知之非艰,行之惟艰。’此固是也,然知之亦自艰”(《河南程氏遗书》卷一八)。程颐不仅认为知难行难,而且提出知先行后的观点,“君子之学,必先明诸心,知所养,然后力行以求至,所谓自明而诚也”(《河南程氏文集》卷八)。朱熹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,认为知与行都很重要,不可偏废,“致知、力行,用功不可偏。偏过一边,则一边受病”。同时认为知先行后,知轻行重,“论先后,当以致知为先;论轻重,当以力行为重”(《朱子语类》卷九)。无论知易行难还是知难行难,无论知先行后还是知轻行重,都把知与行作了区分,认为知与行是两件事。唯有王阳明独树一帜,明确提出知行合一的观点,“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,行是知的功夫;知是行之始,行是知之成。若会得时,只说一个知,已自有行在。只说一个行,已自有知在”(《传习录上》)。王阳明进一步指出,包括学、问、思、辨在内的知的各个环节都是行的范围,“盖学之不能以无疑,则有问,问即学也,即行也;又不能无疑,则有思,思即学也,即行也;又不能无疑,则有辨,辨即学也,即行也。辨既明矣,思既慎矣,问既审矣,学既能矣,又从而不息其功焉,斯之谓笃仁。非谓学、问、思、辨之后而始措之于行也”(《传习录中》)。
知行合一的思想前提是心即理,“求理于吾心,此圣门知、行合一之教”。在王阳明看来,由于理寓于天地万物之中,容易使人以为心与理是两回事,“心虽主乎一身,而实管乎天下之理;理虽散在万事,而实不外乎一人之心。是其一分一合之间,而未免已启学者心、理为二之弊。此后世所以有‘专求本心,遂遗物理’之患,正由不知心即理耳。夫外心以求物理,是以有暗而不达之处;此告子义外之说,孟子所以谓之不知义也”。王阳明认为,分割心与理,必然分割知与行,“心,一而已,以其全体恻怛而言谓之仁,以其得宜而言谓之义,以其条理而言谓之理;不可外心以求仁,不可外心以求义,独可外心以求理乎?外心以求理,此知、行之所以二也”(《答顾东桥书》)。分割知与行,就是被私欲蒙蔽了,“爱因未会先生知行合一之训,与宗贤、惟贤往复辩论。未能决,以问于先生。先生曰:‘试举看。’爱曰:‘如今人尽有知得父当孝,兄当弟者,却不能孝,不能弟,便是知与行分明是两件。’先生曰:‘此已被私欲隔断,不是知行的本体了。未有知而不行者,知而不行,只是未知。’”(《传习录上》)王阳明强调,知与行必须合一,“知行工夫本不可离;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,失却知、行本体,故有合一并进之说,真知即所以为行,不行不足谓之知”(《答顾东桥书》)。
知行合一是批判知行脱节。作为道德价值和实践,知与行客观上容易出现知而不行和行而不知两种常见的脱节现象;如果主观上被私欲所蒙蔽,则会出现严重的知与行脱节问题。知行合一既批判客观可能存在的知行脱节,更批判主观导致的知行脱节问题。在王阳明看来,古人已经批判了行而不知,“古人所以既说一个知,又说一个行者,只为世间有一种人,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,全不解思惟省察,也只是个冥行妄作。所以必说个知,方才行得是”。古人也批判了知而不行,“又有一种人,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,全不肯着实躬行,也只是个揣摸影响。所以必说一个行,方才知得真。此是古人不得已补偏救弊的说话”(《传习录中》)。王阳明认为,知行合一主要是为了批判纠正当时存在的知行脱节问题,“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,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工夫,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,故遂终身不行,亦遂终身不知”(《传习录上》)。知行脱节,一方面给读书人造成了危害,“记诵之广,适以长其敖也;知识之多,适以行其恶也;闻见之博,适以肆其辩也;辞章之富,适以饰其伪也”。另一方面给社会风气造成了危害,“相矜以知,相轧以势,相争以利,相高以技能,相取以声誉”(《传习录中》)。王阳明极力倡导知行合一,就是为了匡救时弊,“逮其后世,功利之说日浸以盛,不复知有明德亲民之实。士皆巧文博词以饰诈,相规以伪,相轧以利,外冠裳而内禽兽,而犹或自以为从事于圣贤之学。如是而欲挽而复之三代,呜呼其难哉!吾为此惧,揭知行合一之说,订致知格物之谬,思有以正人心、息邪说,以求明先圣之学”(《书林司训卷》)。知行合一还要纠正言行不一,“如今一说话之间,虽只讲天理,不知心中倏忽之间已有多少私欲。盖有窃发而不知者,虽用力察之,尚不易见,况徒口讲而可得尽知乎?今只管讲天理来顿放着不循,讲人欲来顿放着不去,岂格物致知之学?后世之学,其极至,只做得个义袭而取的工夫”(《传习录上》)。言行一致,就不能投机取巧,必须自始至终地为善,自始至终地去恶,“今焉于其良知所知之善者,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实为之,无有乎不尽。于其良知所知之恶者,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实去之,无有乎不尽”(《大学问》)。
知行合一是恢复知行本体。“圣贤教人知行,正是要复那本体,不是着你只恁的便罢。”(《传习录上》)王阳明从主观方面看待知行本体,认为知行本体不仅仅是知行合一,而是知行本一,“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,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”(《答顾东桥书》)。真切笃实和明觉精察都具有主观性,只要满足这些主观条件,知就是行,行就是知。知行本体更强调主观的作用,实质是要求知统率着行,行统一于知。王阳明在与徐爱舟中论学时反复加以论证,先是以《大学》说明知行本体,“故《大学》指个真知行与人看,说‘如好好色,如恶恶臭’。见好色属知,好好色属行,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,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。闻恶臭属知,恶恶臭属行。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,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”。接着以孝悌说明知行本体,“就如称某人知孝,某人知弟,必是其人已曾行孝,行弟,方可称他知孝知弟。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弟的话,便可称为知孝弟”。最后以疼痛、寒冷和饥饿说明知行本体,“又如知痛,必已自痛了方知痛;知寒,必已自寒了;知饥,必已自饥了。知行如何分得开?此便是知行的本体,不曾有私意隔断的。圣人教人必要是如此,方可谓之知,不然只是不曾知”。知行本体的基础还是心,心是知行本体的主宰,知与行都是由心所生,随心而行,“如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,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,意在于仁民爱物即仁民爱物便是一物,意在于视听言动即视听言动便是一物”(《传习录上》)。
知行合一是要在意念上为善去恶。王阳明有一句名言叫做“破山中贼易,破心中贼难”(《与杨仕德薛尚谦书》),这说明在道德实践中,善的知比善的行更重要,恶的念头比恶的行为更难清除。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,就是因为知行分离,容易使人轻视知而重视行,不注意从思想上克服不善的念头,最终导致了恶的行为,“今人学问,只因知行分作两件,故有一念发动,虽是不善,然却未曾行,便不去禁止”。知行合一,就是要在思想源头上树立善的理念,清除恶的念头,尤其是一念发动时就要为善去恶,“我今说个知行合一,正要人晓得,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。发动处有不善,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,须要彻根彻底,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,此是我立言宗旨”(《传习录下》)。知行合一,要扫除私欲,荡涤声色货利,“问:‘声色货利恐良知亦不能无。’先生曰:‘固然,但初学用功,却须扫除荡涤,勿使留积,则适然来遇,始不为累,自然顺而应之。良知只在声色货利上用功,能致得良知精精明明,毫发无蔽,则声色货利之交,无非天则流行矣。’”知行合一,要控制调节人的情感。人的情感本身无善恶,有所执着即是恶,“喜、怒、哀、惧、爱、恶、欲谓之七情。七情俱是人心合有的,但要认得良知明白”;“七情顺其自然之流行,皆是良知之用,不可分别善恶,但不可有所着。七情有着,俱谓之欲,俱为良知之蔽。然才有着时,良知亦自会觉。觉即蔽去,复其体矣”(《传习录下》)。知行合一,更要坚持儒家的常道和扩充仁义礼智之心,“通人物,达四海,塞天地,亘古今,无有乎弗具,无有乎弗同,无有乎或变者也,是常道也。其应乎感也,则为恻隐,为羞恶,为辞让,为是非;其见于事也,则为父子之亲,为君臣之义,为夫妇之别,为长幼之序,为朋友之信。是恻隐也,羞恶也,辞让也,是非也;是亲也,义也,序也,别也,信也,一也。皆所谓心也、性也、命也”(《尊经阁记》)。
王阳明心学强调人的自律和主观能动性,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心与理、知与行以及学问与道德、主观与客观分离的矛盾和困难,延续丰富了孟子心学一脉,造就了儒学发展的高峰。同时,王阳明过于强调心的能量和作用,把主观能动性推至极端,又陷入了新的矛盾漩涡。他晚年提出的四句教:“无善无恶心之体,有善有恶意之动,知善知恶是良知,为善去恶是格物”,与其心即理和致良知思想构成了巨大张力,进而引起了弟子及其后学的争论和分裂。尽管如此,王阳明心学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不容忽视,心即理,强调人在道德行为中的主体性,要求人们对自己负责,自觉地做一个有道德的人;致良知,突出良知的优先性,要求人们在做人做事过程中始终坚守端正本心,凸显诚意的修身方法,既不要为物欲所惑,更不要为知识所蔽;知行合一,主张思想意识对于实践行动的决定性,要求人们在“一念发动处”就要为善去恶,以实现人生的圆满。










